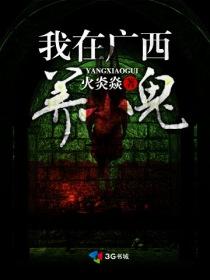怪力小说网>七侯笔录男主角有几个笔灵 > 第二十四章 愁客思归坐晓寒(第2页)
第二十四章 愁客思归坐晓寒(第2页)
一个笔冢吏只能装一支笔,渡笔人却可以同时装数支笔灵。而且从实战来看,这些笔灵的功能可以同时发挥,自如切换,这若是推演下去,可实在太可怕了。
想想看,若是有心人刻意把各种笔灵送入他体内,装五支,装十支,甚至装百支……就算渡笔人天生无法与笔灵神会,只能寄身,可架不住数量多啊,很快便能培养出一个同时发挥出几十支笔灵功效的笔冢吏,其威能惊世骇俗,堪称笔冢世界核武器级别的怪物。
这是任何笔冢吏都不愿见到的局面,势必要把渡笔人除之而后快。这与人性无关,实在是天生相克。
想到此节,罗中夏顿时口舌干燥,没想到今天是自投罗网来了。他下意识想转身拔腿跑开,可一低头却发现,双腿被不知哪儿来的茅草给缠住了。这屋子里明明是木制地板,上头还打了蜡,光溜溜的,什么时候长满了这许多茅草?而且这一簇簇茅草丰茂厚实,叶宽梗韧,似乎已经长了几年,比绳索还结实,罗中夏用力动了动腿,竟是纹丝不能挪。
他哪里还不明白,这是韦定邦发难了,下意识要驱动青莲遗笔对抗。可就在选择诗句的一瞬间,一股苍凉凄苦之感如秋风吹入心扉,顿生忧伤郁闷,一时间根本提不起吟诗的兴头。那茅草趁机又蹿高了数尺,眼看要把罗中夏裹成一个草人。
罗中夏万念俱灰,心道罢了罢了,竟然闭上眼睛束手待毙。
彼得和尚在一旁见势不妙,冲韦定邦大叫道:“父亲,你这是做什么?”韦定邦坐在轮椅上,沉着脸道:“你这么聪明,该知道渡笔人对笔冢吏来说意味着什么。”
彼得和尚怒道:“罗中夏是咱们韦家的客人,岂能言而无信,见利忘义!”他平时总是那一副温文优雅的面孔,这一刻却化为金刚怒目。
韦定邦面对儿子质问,却丝毫不为所动,继续驱动茅草去缠罗中夏。彼得和尚一个箭步要冲到罗中夏身边,双手合十,要去挡住韦定邦的攻势。韦定邦知道这孩子专心守御之术,虽无笔灵在身,但若摆出十成守御的架势,寻常笔冢吏也奈何不了。
这个儿子性格倔强迂腐,用言语是说不通的。韦定邦微微叹息了一声,分出一道茅草去缠彼得。彼得双目厉芒一闪,扯开胸口佛珠,大喝一声:“散!”那一粒粒佛珠竟然把茅草丛撞开一道缝隙。可这时韦定邦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了过来:
“情东,纵然你有心救他,可面对一族之长的笔灵,也未免太托大了。”
话音刚落,一阵秋风平地吹过来,屋中顿生萧瑟之意。黄叶旋起,茅草飘摇,无数的碎叶竟在风中构成了一支长笔的轮廓。那笔杆枯瘦,顶端似还隐然有个斗笠形状。
彼得和尚眉头紧皱,双手却丝毫不肯放松守势。他对韦定邦的笔灵再熟悉不过了,这支笔赫然是与李白齐名的杜甫秋风笔。
杜甫以苦吟著称,诗中悲天悯人,感时伤事,饱含家国之痛,加上他自己际遇凄苦,曾有“八月秋高风怒号,卷我屋上三重茅”之叹,其笔灵遂得名“秋风”。至于那瘦笔之上的斗笠,其实还和青莲笔颇有关系。当年李白曾经在饭颗山偶遇杜甫,戏赠一首调侃他的造型:“饭颗山头逢杜甫,顶戴笠子日卓午。”杜甫一生十分敬仰李白,因此笔灵也把李白的形容保留了下来。
那如臂使指的茅草,自然就是杜甫所吟“三重茅”的具象。其实秋风笔的威力,远不止此,它攻伐手段不多,强在守御控场,必要时可以化出方圆数丈“沉郁顿挫”的领域,能令对手深陷其中,动弹不得。这四个字,乃是杜甫自我评价,历来为方家所推许,乃是杜诗之精髓所在,其形成的结界威力,自然不容小觑。
可惜自从那次大战伤了元气,韦定邦只能发挥出秋风笔威力十之二三,但对付罗中夏却是绰绰有余。
彼得和尚深知此节,因此拼命僵持,只要挨过一段时日,韦定邦残病之躯必然后力不济,便有可乘之隙了。韦定邦也看出自己儿子的打算,他冷哼一声,抬起一个手指道:“兵!”
彼得和尚听到这一个字,惊而抬首:“您怎么连这个都恢……”话未说完,整个人已经被一团碎叶罩住,里面车辚辚,马萧萧,有金属相击的铿锵之声,与哭声汇成一场杂音合唱。
杜甫秋风笔展开的“沉郁顿挫”结界,分作数型。这一型取的是《兵车行》意境,有车、马、兵刃、哭别等诸多声响混杂一处,此起彼伏,百音缭绕,最能削人斗志。彼得和尚没料到,一下子被困在其中。韦定邦抬起头来,望着秋风笔喃喃道“居然还有力量使出这一型来”。
彼得知道秋风笔只能困敌,不能伤人,但若想闯出去也绝非易事。他心念电转,朝着旁边被困在茅草里的罗中夏喝道:“快!沙丘城下!”
杜甫一生最敬仰李白,所以理论上青莲笔是可以克制秋风笔的。李白写过几首诗给杜甫,彼得和尚让罗中夏念的是其中一首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,也是描写两人友情最真挚的一首。青莲遗笔若是将此诗用出,当能中和秋风笔的《兵车行》结界影响,彼得和尚就能得以喘息。
可是罗中夏那边,却是置若罔闻,一点动静也没有,任凭茅草蔓延上来。彼得心中一沉,这家伙本来就如同惊弓之鸟,斗志不强,一心想退笔避祸,如今突遭袭击,恐怕韦家人的信用在他心目中已轰然破产,再无半点战斗的欲望。
他犹不甘心,还想再努力一下。那秋风笔已是秋风劲吹,结界大盛,一股无比巨大的压力压在彼得和尚身上,有如山岳之重。彼得实在支撑不住,终于眼前一黑,晕了过去。很快有无数茅草如长蛇攀缠,把他裹了个严严实实。
韦定邦看到大局已定,这才收起秋风笔,面容比刚才更加苍白,忍不住咳出一口血来。他的健康状况十分糟糕,刚才勉强用出《兵车行》,已突破了极限。韦定邦看了眼被茅草紧紧捆缚住的两个草人,颤抖着抬起右手,想去摸摸彼得和尚的脸,可很快又垂下去了。刚才的一战耗去太多精力,他已是力不从心。
“畏人千里井,问俗九州箴。战血流依旧,军声动至今。秋风啊秋风,不知我还能看你多少时日……”
这是杜甫的绝笔诗,此时韦定邦喃喃吟出来,那秋风笔在半空瑟瑟鸣叫,似有悲意传来。韦定邦勉强打起精神,抓起旁边一部电话,简短地说了四个字:“定国,开会。”
当天晚上,韦家的几位长老和诸房的房长都来到了内庄的祠堂内,黑压压坐了十几个人,个个年纪都在六十岁上下。祠堂里还有几把紫檀椅子是空的,前一阵子因为秦宜的事情,族里派出许多人去追捕,来不及赶回来。
韦定邦坐在上首的位置,韦定国站在他身旁。电灯被刻意关掉,只保留了几支特制的红袍蜡烛,把屋子照得昏黄一片。
听闻渡笔人和青莲遗笔此时就在韦庄,长老和房长们的反应如同把水倒入硫酸般沸腾,议论纷纷。也不怪他们如此反应,青莲现世这事实在太大,牵涉到韦家安身立命之本,是这几百年来几十代祖先孜孜以求的目标。
更何况还有一管点睛笔在。
青莲、点睛,管城七侯已得其二;如果凑齐管城七侯,就有希望重开笔冢,再兴炼笔之道。长老、房长们从小就听长辈把这事当成一个传说来讲述,如今却跃然跳入现实,个个都激动不已,面泛红光。唯有韦定国面色如常,背着手站在他哥哥身旁默不作声。
“关于这件事,不知诸位有什么看法?”韦定邦问道。
“这还用说,既然青莲笔和点睛笔已经被咱们的人控制,就赶紧弄回来,免得夜长梦多!”一个房长站起来大声说道。他的意见简洁明快,引得好几个人连连点头。
这时另一个人反问道:“你弄回来又如何?难道杀掉那个笔冢吏取出笔来?”那个房长一下子被问住,憋了半天才回答道:“呃……呃……当然不,韦家祖训,岂能为了笔灵而杀生?”那人又问道:“既不能杀生,你抓来又有何用?”房长道:“只要我们好言相劝,动之以情,他自然会帮我们。”“他若不帮呢?”“不帮?到时候不由得他不帮。”“你这还不是威胁?”
另外一位长老看两人快吵起来,插了个嘴道:“你们搞清楚,那可是传说中的渡笔人,就算青莲笔能放,他也不能放,万一被诸葛家抓去,只怕就无人能制了。”
头一位长老斜眼道:“既然渡笔人就在韦庄,为何咱们韦家不去改造一下,先发制人去干他诸葛家?”另一长老道:“你打算怎么说服渡笔人真心为咱们所用?”“嘿,这不是又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了!渡笔人该怎么处置好?杀不得,劝不得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