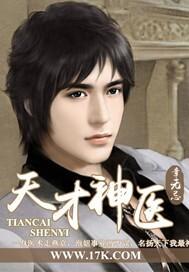怪力小说网>入戏里的经典语录 > 第69章(第2页)
第69章(第2页)
临去时,白蕊回头看了缨徽一眼,面露忧虑。
两人退下后,李崇润走向螺钿床。
缨徽这才察觉,他步履踉跄,身上酒气浓郁。
她想要起身搀扶。
可是身上疼得厉害,刚探出身,牵动伤口,疼得拧眉。
李崇润忙扑到她身边,将她摁回床上。
他面颊上有两酡殷红,一笑,露出亮白的贝齿。
弯身环住缨徽的腰,乐呵呵:“阿姐,我不是在做梦吧,我们真的有孩子了。”
缨徽低眸抚摸他的鬓发,如从前那般。
那些相依相伴的苦涩辰光,那些寒风呼啸的孤寂夜晚。
两人就是这样抱着,说一说心事。
缨徽心中一恸,“七郎……”
李崇润从她怀中抬头,恰捕捉到她眼底晶莹的泪光。
“怎么了,徽徽?”
他一下很紧张,抬起她的脸,无措地问:“你哪里不舒服?”
缨徽忍下泪意和其他,娇嗔:“身上有些疼。”
李崇润忙要叫女医来看,被缨徽制止。
“女医说过,生产后就是这样,要好好将养。白蕊和红珠已给我上过药,这些日子大家都很疲惫,让她们歇息吧。”
李崇润又细细询问了几句,确认她无碍,这才作罢。
不久,侍女奉上了滚烫的古楼子。
酥饼内夹着鲜嫩的酱烧羊肉,一口下去,汁水带着浓郁的香气浇了满口。
缨徽第一回吃这个,是随沈太夫人去清泉寺祈福时。
红珠那馋猫寻摸了来,味道十分惊艳。
她被关在后院,轻易出不得门。
李崇润就趁出去办差,常常绕去寺庙外给她买了来。
羊肉凉了膻气重,不好吃。
李崇润就把古楼子放在怀里暖着,找机会偷摸儿地溜进缨徽的小院子里塞给她。
吃起来还是从前的味道,只是心境大不相同。
缨徽满腹的心事,只有化作食欲。
她需得尽快把身体养好。
李崇润不时捏着帕子给她擦嘴,边擦边说:“静安侯来了书信,说他已辞去中书舍人一职,不日将携家眷离京,直奔幽州而来。”
缨徽了然:“他知道我生了孩子,地位稳固,所以就来了。”
往常,李崇润少不得和她一起揶揄这不靠谱的爹,可今日他神色凝重,几番偷觑缨徽的神色,欲言又止。
偏缨徽心不在焉,没有察觉。
“好了。”李崇润还是决心隐瞒,“你养好身子,从西京到幽州路途遥遥,静安侯拖家带口的,怕是要在路上耗费不少时日。一时半会儿的也到不了。”